AI 信徒是这样一群人,他们相信 AI 技术能够使人类变得更强大。在别人为 AI 可能导致自己失业而担忧时,他们却满心欢喜地迎接 AI 的到来,并且期待着技术的变革能够开启一个平等的新时代。
编剧安宕宕是一位 AI 信徒,她拥抱 AI 的缘由很单纯。在影视行业的权力金字塔架构之下,编剧所拥有的话语权极为微小。传统影视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拉锯战,正在扼杀她亲手创造出来的好故事。然而,AI 时代却有希望让编剧重新获得尊严,使他们能够从一个执行机器回归到真正的创作者身份。传统影视项目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来回挣扎,而新时代的编剧在 AI 的辅助下完成了一整套电影,并且面对着观众打招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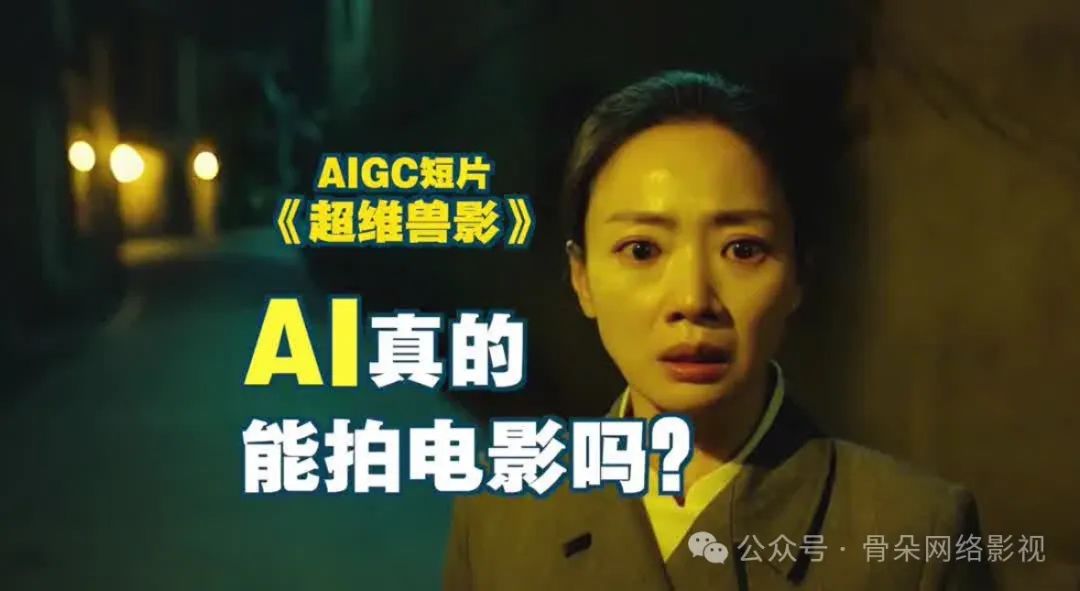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对技术极为乐观的想象。我们在凝视着 AI 世界的数字幻影时,需要看到那些隐藏在算法褶皱里的负面影响。畅销小说家长安野望认为,若创作者完全依赖 AI 创作,很可能会陷入 AI 的框架思维,被 AI 同化。倘若他们不进行突破,或许会终身停留在一种浅层的表达中。
人类究竟该如何驯服强大的 AI 呢?要让它为己所用,而不是被它所驯服。
为什么会成为AI信徒?
你为何会成为一个 AI 信徒呢?在一千个人那里,或许会有一千种答案。然而对于安宕宕而言,答案仅仅只有一个。
AI 能够最大程度地拓展一个个体创作者的能力边界。安宕宕在说出这句话时,身着一身粉红色的皮衣夹克,坐在咖啡厅的座椅上侃侃而谈,那模样就像极了赛博朋克时代的精神导师。实际上,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编剧、大学讲师,同时也是一位 AIGC 研究者与创作者。
安宕宕参与过许多部获奖短片的创作。她的原创剧集还获得了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剧集奖。因为她亲手孵化了多个原创项目,所以她深深了解当下影视大环境对个体创作者的挤压,以及在传统影视流程中创作者被外界强加的痛苦。
传统影视开发的各个环节都在扼杀好故事。其一,干涉剧本创作的人数量过多。大家都觉得自己更了解观众。尤其在前期策划阶段,剧本创作环节成了所有人的认知较量之地。出品方、导演、制片人、策划等,都在要求应该那样去写,将编剧当作执行机器,而非故事的顶层架构师。简而言之,编剧没有话语权。
其次在对接平台时,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做主的人。因为大厂的体制,制片人每天都在重复大量机械性工作,被异化后形成了模块化思维。这种流程会研究大量已经过时的爆款剧的情节、桥段和人设,拿着那些属于 A 故事的螺丝钉,强行塞进另一个 B 故事里,从而导致原创剧本的架构和套路化情节根本不符合要求。之前我与一个平台的策划发生了争论。我表达道:“这个人物是个活生生的人。”然而,他却表示:“这是个产品,所以应当按照套路来,应该是这样。”
现在影视项目的开发逻辑并非从创作开始着手。它的本质是一种争利思维。先有资源,然后再创作故事。是一群掌控资源的人在可调动资源的范畴内进行内容生产。而不是与上述情况相反。传统影视行业若不吸纳新的创意和创意人,将会走进一个死胡同。而 AI 能够打破当前的这种僵局。
说到这,安宕宕的脸上不再愁烦,他的眼睛里满是欣喜与激动。仿佛 AI 如同救星一般,即将成为底层创作者的福音。
从职业角度看,AI 能够助力编剧更好地达成构思。倘若编剧独自一人且没有策划时,要产出一个故事是颇为困难的,这是因为缺乏对话的对象。故而,AI 是一个极为不错的交流对象。当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,AI 能够帮我撰写剧本草稿。接着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探讨,这就像是一个来回传球的过程。我需要不断地吸收 AI 给予我的优秀内容,否则我们就无法顺利地开展这个过程。因此,AI 会促使我主动地进行思考,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
二来,从发展的角度来看,AI 不会取代创作者,而是能够让我们从执行机器转变回创作者。在 AI 时代,编剧能够一人承担一支团队的工作,完成电影的全流程制作。传统影视行业的高壁垒很有希望被打通,编剧可以切实拥有话语权,实现对自己作品的完整表达。未来或许人人都能成为导演,许多有创意的人才会借助 AI 来协助创作电影。那一定是一个拼创意的时代,而非拼工种和拼资源。那些稍微欠缺创意的人,亦或是欠缺深度逻辑与架构能力的人,便可以不再依靠影视来维持生计了。
从交互性方面来看,AI 能够拓展编剧叙事的边界,并且能与观众实现良好的交互。如今,许多观众对一个故事的剧情走向存在不满。其实,编剧可以构建一个故事的世界观,邀请用户共同创作。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对这个世界观进行延展。票数最高的剧情能够代表主线剧情的走向,这是因为它体现了大众的意志。AI 若能同步剧情生成视频,那么观众就能够实时观看电影,并且能够实时反馈数据和流量。
安宕宕的超前想象,能够颠覆现存的影视行业生态,同时也打破了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。在传统影视时代,像饺子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,倘若没有资源的扶持,即便创意再好,一百个中也会有九十九个被埋没。
在 AI 时代,或许没有了资源、金钱以及人脉对创作者的限制,创作者能够仅仅凭借自身的创意,去闯出一片天地,而无需再看他人的脸色。技术的变革能够使底层创作者达成真正的创作平等,这或许正是影视圈中有许多 AI 发烧友的缘由。
人类如何驯服AI?
人类创作者驯服 AI 的过程如同在打乒乓球。AI 是较为初级的对手,需用户凭借自身专业知识逐步教导它,以自身节奏与它打球,如此才能让它逐步成长为更厉害的对手,为人类创作者提供更多灵感与帮助,而不会被它的节奏带偏,丧失自身判断。判断力可说是人类在驯服 AI 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能力。
AI 会生成一个内容,倘若你缺乏剧作的基本知识,那么你就无法对其好坏进行判断。并且这种能力是难以被替代的。安宕宕宣称,她去年和创作团队始终在利用 AI 进行协同创作,此创作属于人机共舞的过程,不但效率得以提升,还获得了更多的灵感。她还把自己与 AI 交互的心得,整理成了《AI 生成剧本创作全流程》这门课程。
首先在大纲阶段,我们团队会召开会议来构建故事框架,并且想出基础的人设以及类型等相关信息,接着将这些信息提供给 AI;然后从 AI 给出的草稿当中找出 10%到 20%能够使用的内容,依据这些内容,创作团队会再次开会去探讨故事的主线;之后我们会利用 AI 自动整理录音,从录音中找出故事的主线和主要的情节点;紧接着,我们会进行调试,之后把内容反馈给 AI,让它去细化和润色成分场;最后,对于台词部分,基本上是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创作,因为 AI 写的台词还不是很合适。在这个交互过程中,人类的角色更像是主编剧。AI 则如同助理编剧或者策划。这样一来,我们极大地降低了码字的时间成本和人员成本。
代码开始消化会议记录之后,创作者才真正解放了双手。这样创作者就能够去做那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。安宕宕认为,编剧的核心能力是架构故事的能力,而不是仅仅做低级的码字工作。并且,AI 无法取代的编剧核心,恰恰就是顶层架构能力。
编剧能够构建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世界观。然而,AI 仅仅能够进行模仿和复制。并且,AI 没有能力原创出一个典型的人物。你无法凭借一个基础的模型来判定人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便是剧作的精髓所在。例如哪吒和敖丙的人物关系,不能仅仅用朋友来定义,而是一体两魂,这种关系非常具有创新性。人类对于“人”的研究都还没有完全透彻,目前 AI 的能力是远远达不到的。
长安野望是一位小说家,他曾创作过多部悬疑和科幻畅销书,如《诡墓天机》《双螺旋深渊》《破界爱人》。他也是国内第一批接触人工智能的人群之一。长安野望对 AI 的态度并非完全的技术乐观主义,他觉得 AI 有其局限性,如今 AI 所写出的小说,带有一种小学生努力模仿老师文笔的机械感,缺乏人味儿。同时他也认为AI的长处在于它有一个很强大的数据库。
所以他选择与 AI 共舞的方式,即让 AI 成为自己的外挂大脑。他在创作时,首先自己会迸发出一个灵感碎片,例如地球上的水全部都被吸干了,然后会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AI 会协助我对这个假设之下在货币、社会以及建筑层面所发生的一系列结果进行推演。当我获取了全面的信息后,我会把这个故事创作得更为真实。因此,我将它当作一个超大型书架和资料库来使用。目前,AI 能够给予我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拓展视野、发散思维,并发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。
在拥抱 AI 时,长安野望很警惕不被同化。他一直坚持自己写正文,就是为了在 AI 时代守护自己的语言风格。一个成熟作家会形成自己的文风,这很珍贵且不可替代。很多头部作者有自己的语言风格,也有喜欢这种风格的粉丝,他们被 AI 淘汰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。新人作者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,套路文的作者,他们会最先感受到寒冬的到来。

AI 在影视圈可能会引发一场平权革命,而在网文界或许会掀起一场内卷风暴。有编辑预测或许会有平台推出全 AI 小说,那样一来可能会进一步压缩人类创作者的市场空间。人类创作者与 AI 的密切互动,不仅会使 AI 更像人,也会让人类更像 AI。
长安野望觉得:创作者若依赖 AI 创作,就很可能陷入 AI 的框架思维里。倘若他们不进行突破,或许就会一辈子停留在浅层表达中。所以在人类与 AI 的关系里,我们得先弄清楚谁是主谁是仆。要是未来我们把 AI 当作主人,那未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作品都将由 AI 来生产。它会同化我们的语言体系,会影响我们对故事的审美,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习惯,它将重新塑造人类的生活。
AI会取代你吗?
即便身为对技术前景极为乐观的 AI 信徒,当面对持续进化的 AI 时,心中也会思考“AI 是否会取代人类”这一终极问题。此问题看似遥不可及且宏大,然而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就如同一块从斜坡上滚落且不断加速的巨石,迫使每个人去思索自身存在的价值。
安宕宕把咖啡放下,然后从容地说道:“我并不担心 AI 会取代我。因为当下的 AI 尚未达到完全替代我的极限,我会和它一同去探寻更多的可能性。然而倘若有一天 AI 连故事的架构都能够完成,并且灵感能力也超越了我,那我就可能会下岗。尽管我作为人类不希望 AI 会取代人类,可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和迭代的一个过程。”如果跳出人类的狭隘视角,我会觉得 AI 更智能。AI 的视角并非二元对立的。例如,当我问它一个哲学问题时,它能够跳出既定框架,从心理学角度和自然科学角度去解答问题,反而能找到新的钥匙。
长安野望期望人类与 AI 能够和平共处。他不希望 AI 抢走自己的饭碗,同时也不会排斥 AI。在短期内,他自己并未感受到特别大的威胁,因为他所写的是科幻悬疑赛道的小说,而这两个赛道的小说要想复制起来是比较困难的。长远来看,我认为 AI 的出现并非是要取代我们,而是要让人类的大脑神经电流与 AI 网络上的数据流一同去编织美好故事。故事塑造了人类的文明,从远古延续至今。实际上,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,我们都应当保存自己心中的那团火苗,守护人性中的那缕微光。
最后,骨朵把这个问题抛给了 AI,DeepSeek 的回答是:AI 的真正价值在于进行扩展,而不是替代人类的能力。如果技术崇拜转变为新蒙昧主义,那么我们或许需要再次提起启蒙运动的口号——“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!”
骨朵认为这句话很适合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。到目前为止,AI 仅仅是一个工具。虽然它的机械算法很强大,然而它终究没有人类的灵魂,也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。在机器理性的视角下,人性的矛盾、犹疑、复杂、多变被视为数不清的 bug,但这恰恰是人类不会被 AI 取代的部分,同时也是人类创作者作品的精髓。或许我们应该更加自信。AI 是来帮助我们的,并且能让我们平等地去干翻这个世界,而不是来干翻我们。
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,作者是未盈。36 氪获得授权后进行了发布。
本文采摘于网络,不代表本站立场,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:http://mjgaz.cn/fenxiang/274490.html

